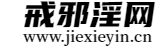相學大師韋千里講述:見色不淫,桃花化為財運
作者:無名氏 返回目錄 0 位書友評論
選自:韋千里——《知命識相五十年》
時間(1937-1945 年),地點:上海
現在老梁是老陳的上司了,他是維新政府的首領。被天一星說準了他的命相,有一天派人送給天一星白米十包,現金二千元表示謝意,并約他吃便飯。吃飯那天老梁并沒有邀請政府的要人,因為這是私人間的酬酢,而且對方是一個算命先生,此事又是迷信之類,所以他只約了幾位自己的親信,大都是機要秘書、總務科長之類。當然,老梁的用意也希望能借此機會請天一星替這小群自己的心腹看看相,是不是六親同運,最重要的請天一星看看對自己有沒有沖克;因為那時抗戰的地下軍事人員正在上海展開暗殺漢奸,老梁深怕自己心腹中有問題,那就太危險了,所以在入席之前,他曾囑天一星替他留意今天一起吃飯的人,對他有無沖克。
于是在吃飯的時候,天一星就對同席的各位相局和氣色都留意細看一下。當中有一個姓杜的先生,儀表十分出眾,年紀大約三十出頭,天一星問他說:“杜先生,你今年貴庚?”他答說:“三十四。”天一星又問一個姓蕭的:“蕭先生,你的貴庚也差不多嗎?”他答說:“我們兩人同年,我比他大三個月。”接著他們兩人就同天一星請教,最近這幾年后運如何。天一星笑笑地說:“今天梁先生賞飯,各位又都是梁先生的親信,我當然用不著說各位都是貴人相;但我們既然有此一面之緣也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我得看看各位有沒有什么地方,需要對各位之中有所貢獻。”“對的,君子問禍不問福,我們這一班人,都是托梁先生的洪福的,目前當然都不錯。”
有個黃先生這樣說:“不過,目前的時局對我們是不利,所以我們還是問問此后我們的安全第一問題。”“先生,你看得出這戰事要到什么時候可以結束呢?”另一個人這樣問:“這戰爭到底對我們有利還是有害?”“看來總是有害的,戰事哪有對我們有益的道理呢?”
天一星先生又笑笑地說:“那也不一定,凡是有利必有弊,戰事之所以發生,原因由于雙方都認定對自己有利,所以才會爆發戰爭;但事實上大都是兩敗俱傷的。
至于這場戰爭對于各位的利害問題,依我的看法,則是對各位有利,我看各位的相,都是由這場戰事而轉好的。”這句話把在座諸人都說得好笑了,他們心中想他們都是一班小新貴,的確乃由抗戰發生才有這機會跟著老梁參加這偽政府,于是他們就關心問到戰事的結局問題。“關于戰事的結局如何我是不敢說的。”天一星說:“但我從梁先生以及現在從各位的相局看,這戰事要到八年之后才能結束的。至于如何結束。結束時對各位的情形如何,我也不知,到了那時,各位自然會明白的。”
接著那位杜先生就問:“先生,剛才你曾特別問到我和蕭先生的年齡,是否有什么特別事故?無論是好是壞,我們都希望你能不客氣地指教,我們是問禍不問福的。”
天一星又笑笑說:“你們雖然要問禍,而我卻是為你們二人說福。不過,福也有多種,有的是洪福,有的是清福,也還有是濁福的。洪福像梁先生這樣是難得的,一般人大都是濁福的。”他看了杜先生和蕭先生兩眼之后又說:“我看你們兩位特別喜歡的還有一種福,我想你們各位也許會曉得他們有什么特別福的!”
于是各人當中有的說他“食福”很好,也有的說他“衣福”很好,因為蕭先生當時就穿著新裁的筆挺西裝,也有一個說他倆還有一種福,但他不肯說出來,因為那福是許多人不知道的,而他本人也不愿意人們知道的。
“對了,我說的杜先生和蕭先生的特別福就是這福,是你年輕的人都喜歡的‘艷福’,對嗎?”天一星說了之后,大家都笑起來。而杜、蕭兩位呢,卻也難免臉皮有些發紅,笑嘻嘻地已在承認他們自己的艷福了。
“不過,”天一星說:“艷福分正與邪兩種:正的艷福是妻賢妾美,而邪的艷福則是尋花問柳,到處風流,最重要的,正的艷福對財運有利,而邪福則對財運有害,甚至有其它災禍,所以有艷福之人不能不謹慎了!”
杜、蕭兩人肚子里好似想問什么,而嘴里又說不出來樣子,還是剛才說曉得他兩位有特別福的那位先生就說:“那么,請教先生,他們兩位到底是正還是邪呢?”
天一星先生說:“我剛才特別問他倆的年齡,就是為了這事,如果他們是正艷福,在命理上也就是正桃花,那就不用說什么了,就是因為他們兩位都不是正福,同時是有災禍的,所以我才特別要請他們注意了。”
那人又解釋說:“但他們似乎也很快樂,他們的太太很大度,不大管他們,并沒有什么麻煩之事發生過。”
“是的,”天一星說:“在他們三十四歲之前不會有什么麻煩,但明年起,他倆開始行眼運,在三十五至三十八歲這四年中,他們必定有新的桃花運,如果不想避免也像過去一樣的話,那災禍便要立至的,如果今天肯接納我的話,明年起,對新的艷遇力求避免,那么,逢艷退避、見色不淫的結果,不僅一切順遂,還可能逢艷化財,官運財運都會亨通的。”
此時,杜先生就開口問:“先生,你看我們兩人是否因為是同年關系,所以都有這毛病?我們的情形是否以后都是一樣的?肯避免的話,是否可以避免呢?”
“如果肯避免,總是可以避免的。”天一星說:“不過,依你們的相局看,彼此卻有不同之處,杜先生的艷福大都是飛來的艷福,是女人對他有意的;而蕭先生的艷福則大都是招來的,是他對女人施展手腕的。”說到這里,在座中各人都哈哈地笑起來,表示天一星這話又說對了。蕭先生自己聽了難免臉紅耳赤,覺得沒趣。
但天一星卻又接著說:“那是沒有辦法的事,這是命相注定的了,沒有辦法的,各人有各人的不同艷福。在座各位之中,有的人很想有艷福,但不是一生得不到美人的垂青,就是自動地愿做美人的奴才也還沒有福氣的。”大家又大笑起來了,因為其中確有一個姓姜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男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常常碰女人的釘子的。
“他們兩人還有什么不同的沒有?”其中有人這樣問。“以后你們兩人同樣都是有災禍的嗎?老杜既然是飛來的艷福,那末他是否可以免于災禍呢?”
蕭某又說:“我老是不肯避免的話,可能有何種的災禍呢?不太嚴重吧?若是這一切都與命相關系的話,為什么又可以避免的呢?”
天一星此時似乎正經地對他們解釋其中的道理。他說:“本來飛來的艷福和招來的艷福是有不同的,招來的當然不如飛來的;如果一生只有一兩次飛來的艷福,而能守住這艷福,那就一定屬于貪色與好淫,而災禍也就難免了。”他加重口氣地說:“大家要知,艷福可以飛來,橫禍當然也可以飛來,而且比其它橫禍都嚴重。”
“我們兩人是否明年就有橫禍?是舊事所引起的橫禍,還是明年新事所引起的橫禍?”蕭某問道。
“不是舊事,而是新事。”天一星說:“我不是說過的嗎,你們兩人的平安艷福只到今年為止了,明年以后,開始走眼運,就不可再有女人之事了。過去,你們兩人都是從二十四歲起走桃花運,已經走十年了,對嗎?”杜和蕭兩人,默默地想了一下,輕輕地點點頭,表示天一星所說的并沒有錯。天一星就繼續說:“我可以斷定你們,這十年來,你們兩人沒有做好的事,除女色之外,其它的事都是不滿意的。而且,你們兩人也不曾做過足兩年的事,都是幾個月至多的也不過一年幾個月就要變動的;因為你們差不多每兩年就有一次艷遇。”
“明年夏天起,如果再有艷遇之事,千萬不可太隨便了。”天一星繼續說:“在這四年中,就是從明年三十五歲至三十八歲,如果仍舊見色思淫的話,不管那艷福是招來的也好,飛來的也好,其所造成的災禍,不僅破財而已,最少要傷害身體,要流血之事,甚至殺身之禍!”
那天在宴會席上,天一星對杜某、蕭某兩人所作的斷語只此而已。他只是指出其利害,并不加以斷言兩人將來是如何,因為依他的看法,這災禍是可以避的,但老不想避,那就只有任其發生災禍了,輕的流血,重的殺身。
第二年的春天,老梁到北平去和“臨時政府”的首要舉行會議,他是代表南京“維新政府”的。他原是一個老風流人物,又曾是北洋政府的政要,此次到了北平,又以新實的姿態出現,而“臨時政府”諸首要又大都是舊官僚軍閥,于是若干天的會議之后,就是在花天酒地中酬酢了,老梁自己也想不到,竟然看中了一個二十一歲的妓女,在臨時政府諸政要的捧場之下,用八千元的身價把她贖出納為小妾了。納妾的儀式就在故都舉行。
幾天后,由北平一起坐日本的專機回到上海,老梁把她藏嬌于上海北四川路底虹口花園附近的竇樂安路的金屋里。這地方有幾所花園洋樓,上等住宅,路上既有日本的海軍陸戰隊站崗,而各新貴的住宅門口又有維新政府的警察把守,出入有保險汽車,再有保鏢隨從,這藏嬌之地總算最安全沒有了。
老梁納妾的喜訊一傳出去,新實們當然要向他慶賀一下的。請客那天,老陳也由杭州趕到上海。觸景生情,老陳想,自己和老梁的年紀差不多,他已有妻又納妾,而自己自去年那位黑巿夫人卷逃之后,還是孤孤單單的。
此時,老梁是老陳的上司,上行下效,老陳不久也娶了一個上海會樂里的妓女為外室。因為老陳元配在世,而且生了三個男孩,很有權力,老陳只好偷偷摸摸的在外室藏嬌,卻不敢公開納妾。
南京到上海和杭州到上海的路程差不多,都只是幾個鐘頭的火車可以到達的。所以老陳的外室也設在虹口區,為的是他們各家彼此可以照應,而她們之間也可以在老爺不在家時有伴,來來往往。
湊巧的是,當時偽組織的上海特別巿巿長傅某被抗戰的地下工作人員暗殺掉,上海特別巿政府改組,南京維新政府就派人參加。這上海特別巿政府是成立于南京維新政府之前,直屬于日本軍事機關的。所以到了此時南京維新政府才有機會派人參加。除由日本人同意派二三個上層的人參加外,也派幾個科長級人員參加。而杜某和蕭某二人,因為對上海社會頗熟悉,就被派來當科長了。
這兩位三十五歲的年輕小新貴,除巿政府科長的職務外,為著各種便利,他倆就負責平時照顧虹口區各政要的公館,以及每次接送南京和杭州兩地的政要事宜。因此,杜某與蕭某二人,就很自然的和政要的家眷有接觸的機會了。
那時候,虹口區內南京和杭州兩地新貴的明暗外室約有二十家之多,家家都需要杜科長和蕭科長的照顧,一時這兩位科長便成為二十家的紅人。很快的,他們兩人便成為虹口區姨太太們的忙人了。他倆日夕都在這群雌粥粥之中奔走,無形中,有點像女兒國的兩個男子了。
最初還是蕭某向老陳的外室施展吊膀子的故技。老陳的外室小名紫萍,原系會樂里的妓女,老爺既然常在杭州,她獨居虹口難免孤寂,于是一拍即合,蕭某果然又走桃花運了。老蕭雖然見色思淫,故態復萌,但他也不曾忘記天一星去年對他所說的話。但他又環顧當時的環境,當時暗殺風熾,老陳每次由杭州來上海必先打長途電話通知家里,再由家里電話通知老蕭,由他帶了保鏢和汽車在火車站接他的。此事是不會被老陳識破的。
同時,他知道自己和老杜二人是虹口區的一號紅人,而平日和各家中的下人們也極其相好,而且,關于姨太太交男友之事,在上海是一種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之事,就是被下人們看出,也不至于有什么的。這老蕭的想法自認并沒有錯,在他的勢力區內不至于有災禍的。和老蕭差不多是同時,老杜也果然又有飛來的艷福,而且同時飛來約有三個之多。三個女人是夏太太、周太太和梁太太。真想不到,這位梁太太就是老杜上司老梁由北平娶回來的愛妾。她原是蘇州蕩口地方地道的美女,自幼被父母賣給北平鴇母當妓女的。蘇州是出美女的有名之區,而美女卻不是出于蘇州城里,而是生于蘇州西南面一個名為蕩口的鄉村一帶。上海和北平、天津妓院里的鴇母,每年都親自到蘇州來選拔美女作為養女的。當然,誰也知道凡是來蘇州賣女孩的,都是預備長大當妓女的,所以大都向蕩口地區去選擇。
這位梁太太既系蕩口的地道美女,又曾經鴇母的訓練,再當過名妓的經驗,當然在色藝各方面都是八面玲瓏的。只要她心中有意,就是十個老杜也不能逃出她的迷魂計的。不過,現在卻有一個特別的情形,那就是老杜這時是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在她們群雌粥粥的心目中,因為她們的老爺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便成為一個年經的美男子了。所以,除了梁太太之外,還有兩位也都是姨太太。
而且,這兩位夏太太和周太太,也都是堂子出身的名妓,同時也都是蘇州人。因此,由于三星隨月的關系,她們之間彼此既有顧忌,而老杜也弄得無所適從了。老杜本來是一個風流的人物,雖然他一向都是女人來垂青他,而他卻也來者不拒,多多益善的。但此次情形卻有些不同,因為她們都是彼此時常相見的太太們,而且也都住在虹口區附近的地方,在她們之間老杜的一點舉動她們都會知道的,人言可畏,此事若被人傳到夏、周、梁三位大人知道,別的不敢說,科長的職務馬上就要丟掉。因此,老杜不能不顧忌,雖然表面上不得不周旋于三星之間,卻始終不敢作進一步的嘗試,和她們仍保留多少距離。
有一天梁太太率性不客氣的直接問老杜,何以對她若即若離?是否他喜歡夏太太不喜歡她?是否因為周太太對他有什么特別的地方?老杜一時答不出話來。逼不得已,只好把從前算命先生天一星說的話說出來塞責了。他對梁太太說,因為去年梁公請客時,算命先生天一星,也就是前兩年預言梁公會東山再起的人,說他今年有桃花運,但這桃花運是有危險的,所以他不敢嘗試了。但這話不能使梁太太相信,他認為這只是搪塞的話,一個男人不會因為相信命運的話而拒絕女色的。于是梁太太就要求老杜一道去算命,看看是否這樣說。老杜當然不能不答應,就說要到天一星那里去。
然而,梁太太卻另有意見:她說天一星未必可靠,同時,他既然替老杜看過了,當然要和從前的說一樣。她主張到霞飛路張熒堂那里去,因為,張熒堂是一個瞎子,她認為瞎子比開眼的好,他是鐵口直言的。
于是老杜只好陪梁太太到張熒堂那里去。老杜把時辰八字交給梁太太,他自己預備不開口,只是聽,梁太太把老杜的生辰報了之后,張熒堂就問:“這位先生他本人在這里嗎?他是你的什么人?”
梁太太看一看老杜,笑一笑,她好像很得意地表示她之所以選擇張熒堂,就因為他瞎子看不見人,他的推斷命理就不至有何顧忌了。于是她就隨口依她早就預備好了的答:“他本人不在這里,出門做生意去了。他是我的哥哥,想今年娶嫂嫂,看是否合宜。”張熒堂屈指在點算,仰起頭來微笑地說:“不對的,令兄已經有了嫂嫂,而且有了兩個兒子,今年不會娶親的,你不要騙我。”他再堅定地說:“他既是上海人,今年并沒有驛馬,不會出門的。同時,他這個命也不是做生意的命,而是做官的命,目前官雖然不大,但他的權力卻是很大的。他的情形如果像你所說的,那么他的八字就沒有錯,我就可以再說下去,否則就是八字錯了。”
此時,老杜和梁太太相對一笑。梁太太笑笑地表示承認張熒堂的論斷,說:“先生,你說的沒有錯,請你再說下去。”
“你用不著騙我的,我也無法騙你的,你來為的是替令兄看今年流年的運氣,現在已經五月了,本年的事已經發生了不少,我只能就命理論斷,說對了并沒有什么希奇,說不對才算希奇。現在讓我先把過去五個月的情形說一說,如果說對了,那么以后的七個月也會對的。”張熒堂特別問一句:“你真的是他的妹妹而不是他的太太嗎?他的太太也在這里嗎?”
“我是他妹妹,我的嫂嫂不在這里,”梁太太說:“有什么話請你隨便說,你只需照命理說,是好說好,是壞說壞,沒有什么關系的。”
于是張熒堂說:“令兄幾個月來正在走桃花運,看他的八字,顯有拓合和爭奪之象,似乎有兩個以上的女人向他爭奪。不過,截至目前,他還是徘徊兩美之間未有所抉擇。此事希望不要讓你的嫂子知道,知道了,也要勸她不要加以干涉,反而有利,讓他良心良知發現,可能會脫離這桃花劫煞的。因為走桃花運的人,心志難免糊涂,家花不比野花香,太太一干涉,反而把他迫上梁山了。”
“那么,據你看,他是可能脫離這桃花運嗎?如果不能的話會怎樣呢?”梁太太問:“如果他能逃過這美人關,又有什么好呢?那兩三個女人之中,是否都不會達到她們的目的呢?她們對他也有什么不利的呢?”
張熒堂說:“今年是令兄交運脫運的流年,所以今年是難免有重要事情發生的,現在他碰到了妒合爭奪的桃花,就是不利的現象,如果不慎,便有劫煞;如果能避去這劫煞,這桃花就會轉化為財運的。”他又屈指扣算一下,說:“由昨天起,四十五天之內,將是他的重要關頭,若能保持現狀,不因女人之事損德,那就會有飛來的財運;如果有缺德之事,也就是見色思淫之類,那就有飛來橫禍的,希望你想法告訴令兄,無論如何要度過這四十五天。”
老杜聽了就對梁太太看看,眼色的表情是向她請求原諒,讓他維持現狀“樂而不淫”,看看四十五天之內有何好的變化。梁太太看見張熒堂說得這樣確定,時間也在目前的月半之內,也就無話可說了。
事也奇怪,就因為梁太太自己聽了張熒堂的話受了感動,就決心把老杜放棄,讓他免于不利之事而且又有財運好走,便主動地把算命的事告訴了夏太太和周太太,說是大家既是好朋友,也都對老杜有好感,就當讓他走好運。
因為此事原是三個女人成為鼎立之勢,各人有各人的辦法,也有各人的顧忌,現在既然梁太太肯把此事說破了,夏太太和周太太當然沒有話說,因為此事原不能說破,現在既經說破,大家就無所謂了,男人她們并不是沒有見過的,何必一定要老杜呢。于是大家就決定不再與老杜來往了,老杜也趁此機會從此不再和她們混在一起了。說也奇怪,此事還沒有一個月,老梁和老夏、老周三人在南京接到有人的告密信,說老杜和三位姨太太有說不清白的事,老梁本是一個風流人物,從前在北洋政府時代,姨太太偷人乃極平常之事,只要不把丑事鬧出去,原無所謂的。但老夏和老周二人都不然,他倆決定對付老杜。
過幾天老梁回到上海,所目見和根據公館里的用人報告,老杜已不到公館了,和姨太太并無什么不清白的事。有一天他見到老杜,就問老杜何以不常到公館去?老杜也直說:“人言可畏,我要避嫌。”老梁說:“只要我相信你,何必避嫌?人言何必畏?”他說:“我記住去年天一星算命的話,我今年又有桃花運,而且是有不利的劫煞的,所以就是梁公肯相信我,也不能擋得住劫煞,因為這是災禍,是旦夕難保的天災人禍,誰也不能保證的。”
這話卻把老梁提醒了,因為在南京時老夏和老周對他說過此事,而且當時他們兩人曾說過,老梁度量大,不想對付老杜,而他兩位決定對付老杜的。于是他當夜電話約夏周二位見面,問他對老杜之事有沒有什么決定。他們二人說已經決定了,是買了一個法租界里的流氓,預備給老杜吃吃苦頭,意思是要打傷他的身體,如毀容之類,最少也要使他進醫院半年。
老梁立即要夏周二人把此事暫押后兩三星期,等他查明白了再行不遲,如果確有此事的話,干脆就把他干掉算了,何必拖泥帶水呢。夏周二人當然要接納老梁的話,通知兇手暫緩兩三星期,等通知再決定。
過兩天一個晚上,老梁就和姨太太談起夏太太和周太太為人之事。三句話說完,老梁有意的說到老杜身上來。老梁說,夏先生和周先生為了不放心他倆的太太年輕美貌,曾派有密探時常暗中看守他們的家。根據報告,老杜和兩位太太過從甚密,似有曖昧之事,所以他們兩位要想法對付老杜,就問姨太太,他們之間到底有無可疑之處?梁太太一聽見夏周兩位要對付老杜,她知道所謂對付是很嚴重的事,即上海流氓所謂“白的進去,紅的出來”,就是要暗殺的,于是她就對老梁說:“如果夏先生和周先生要對付杜科長的話,那么真是冤枉的事了,而算命的話也不靈了,做好人也沒有用了。”這話當然引起老梁的注意,在追問之下,才明白老杜確然因怕有桃花運劫煞而不敢和她們三位姨太太往來的。老梁既然明白了這事,但因這話乃由自己的姨太太而來,當然不能使夏周二位相信,暫也不告訴他們二位。
過幾天老梁對老杜說,想把他再調南京去任科長。老杜毫無考慮就答應了。接著老杜連上海的家也一起搬到南京去了。因為南京那里的科長是比不上上海特別巿科長的肥缺的,老杜竟然決心連家都帶走,可以證明他確然是怕走桃花運的。老梁此時才把老杜和三位姨太太之間的真相告知夏周二人,不久他們一再細查,也明白了實情。
老杜調任南京僅僅一個月,老梁把他介紹給江蘇省長高冠吾,立即提升他為江蘇省武進縣縣長。老杜的桃花轉化為財運竟然就是這樣間接的轉變,真是妙不可言了。事后老梁和夏周二人談起此事,也驚嘆不已。因為如果當時老杜不調去南京的話,最少他要身受兩刀,臥床半年的。
至于蕭某和陳太太發生曖昧之后,朝夕如漆如膠,毫無忌憚。當然不久傳到老陳的耳朵。老陳因為去年既有黑巿夫人卷逃,現在又發生此事,心中特別不愿。那時他榮任浙江省政府的財政廳長,為著安全,身邊有保鏢三人,保鏢都是上海黑社會的幫中人物,素有義氣之舉的,他們也不征老陳的同意,商議對付蕭某。當時上海的地下特務活動還是很活躍,暗殺之事時常發生。于是三位保鏢就決定利用抗戰的地下活動,來對付蕭某。但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因蕭某的地位還不夠作為特務暗殺的目標;二因暗殺不慎,反而弄巧成拙,于是他們就想一種辦法,利用一次南京偽政府和上海特別巿政府新貴們在北四川路一家名叫“壽”館的日本料店宴會時候,因為老蕭那天也在那里招待客人,在席散之前,他和幾個巿政府科長階級的人員在壽館日本菜館門前準備送客之時,他們事前叫一人突然出現老蕭身邊,拋了一個假的手榴彈,這兩個保鏢這時就同那人開槍,實際他們不是向那人射擊,而是向老蕭射擊,老蕭就應聲倒地了。
事后他們報告說,當時發現三個兇手,一個拋手榴彈作掩護,兩個向他們開槍,他們也還擊,老蕭就在這紛亂之中擊中太陽穴立地斃了的。因為是在夜里,赴宴的人都是中國人,沒有日本人,被打死的又只是一個科長,人們就都以為那三個兇手原是守在那里等待席散行事的,當時剛好蕭科長由里面出來,可能被他們看錯了而作為替死鬼的。于是這班新貴們,不但不去研究老蕭的死因,而且還以為他作了替死鬼是他們的福氣了。那天晚上在壽館里宴會的,老梁、老夏、老周和老陳四人也都在場。各人有驚無險之后就相率驅車到梁公館去談談。而夏太太和陳太太這幾個名妓出身的姨太太也都先后一起到梁公館來秋慰問她們的老爺來了。
這幾位漢奸新貴聽取他們的保鏢把在場所見的情形報告之后,在此生死關頭過了之后,接著又是他們所喜歡談論的命運問題。
頭一個提到老蕭今天死于非命的事,就是老梁。老梁說:“去年天一星命相倒曾說過小蕭今年有危險,若能避過桃花運,那就會化為財運的,為什么我們還沒有聽見他有什么桃色新聞,而會有此事呢?”
此時大家都沒有話說,而陳太太坐在角落里特別裝作鎮靜的樣子。倒是老陳開口說:“他到底有沒有桃花運我們也不知道,明桃花倒不要緊。老是暗桃花,那就是真正作孽的,這事只有小蕭自己明白了,”
關于小蕭和老陳的姨太太不三不四的事,不但老陳自己知道,就是老夏老周也微有所聞的,所以他們聽了老陳這話,也就表示同意,說是算命天一星說的話,明的事既然應驗,那暗的事就恐怕也一定是有的,不會無的。
接著他們很快地又談到老杜身上去。“倒是老杜好,他肯聽算命先生的話,”老周說:“既然相信命運,就應當相信得徹底,不應該有的信有的不信,好的就信,不好的又不信。”
“所以我說小蕭一定有作孽的事,我們只看小杜的
事情就很明顯,他能逃過了桃花運,果然就化為財運了,卻不知小蕭必定死于桃花劫里的。”老夏也這樣說,“據天一星后來又有一次對我說,杜縣長將來還會有更好的財運,那是真正的財運而不是官運。”老梁說:“據說他的官運只到了縣長為止,不能再高升為簡任官了,但他的財運卻是很大,將來會成巨富的。”
小技巧:按 Ctrl+D 快速保存當前章節頁面至瀏覽器收藏夾;按 回車[Enter]鍵 返回章節目錄,按 ←鍵 回到上一章,按 →鍵 進入下一章。